离开银色荒原,是一场「意识逃离」的纪录。 一切始于一对恋人跨越百年的重逢——他曾将自己冻结于时间之外,为等待恋人从机械的身份蜕变为与他同质的“人”。他们约定在醒来之后,于永恒的未来中重逢。然而,当相遇终于落入停格的永恒中,爱却因失去流动而逐渐衰败。在剥夺了消散与变化的“银色荒原”里,一切都沦为乏腻的重复。 这是人类“意识逃离”的起点。 他们开始渴望溃败,渴望短暂,渴望那些会消逝的触碰。他们穿越银色荒原,去寻回被遗落的“自然”。 这注定是一段迷人的旅程,无人知晓他们是否真正抵达,却唤醒着我们对生命流动的再次感知。 或许,离开银色荒原,本就没有目的地。在他们彼此陪伴的追寻中,时间已重新开始流动。意识回到这段被完整书写下来的记录。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冬眠前最后一次去水族馆,他对着金鱼闭目许愿。 机器的恋人在身旁沉默不语,待他结束才开口询问:“你想要怎样的未来?” “我祈求永远,”他与那深藏镜头的双眼对视,“祈求你我同是人类,永恒相守。” 传说中的金鱼为渔夫实现愿望后,又因人类的贪婪而收回了馈赠。面前的金鱼兀自游动,冒昧的人类莫名陷入不安:三个愿望,算是贪心吗?会转而变成诅咒吗? 他们徘徊直至闭馆,在磁悬浮列车的站台告别,准备开启一次遥遥无期的分离。他向恋人递去一封信:“用极难降解的塑料制成的。我不敢赌任何的电子存储介质……但写在纸上的字总可以直接读取。” 信上写明了名字和爱恋,还有一句约定:“未来见。” 短生的人类陷入沉睡,不计年的机器投身变迁。时间开始变作巨大的、无休止的加速器,直到把世界推向某一个进化分支的顶点才能暂停。机器也终于成为符合此刻定义的“人类”;他们终于可以相聚,可以获得永生永恒的爱了。 他醒来得见的就是这样一片安宁纯净,没有错拍或即兴,无需复杂的合成代谢:银色无休地铺展着,永远成为万物的材质,一切凸起的部分——楼房、植物,乃至人类——只像是这片银色上小小的褶皱。 重逢在这样的银色里很美……但随之而来的是因恒定而生的疲倦。一切都很好,面容、体温、心跳,稳固不变,如同常数。可是爱呵,爱需要的是那一点骤生的波动。曾是机器的恋人了解永远比爱多;而一直是人类的他了解爱比永远多。永远和爱的叠加令他们都陌生到不知所措,他们长久对视,再也生不起波澜。 找回爱的唯一线索是那封久远的信件。旧时代的一切都已模糊,唯独只在这封信件的文字里,尚且留有关于鲜活、脆弱、激情的痕迹。他们读信、回忆,想起曾被果汁弄脏的手指,终于唤起了牵手的欲望。 旧时代的人类第一次牵手是为了离开伊甸园。现在,他们要离开银色荒原。 “我们会再次失去这种感觉吗?”恋人的面容上残存着属于自己的第一道泪痕。 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颗生锈的螺栓:“那就沿途把它都写下来。如果找不到那样的地方,起码在返程时,我们还能记起。” 以荒原为纸,他们写信。恋人接过“笔”时迟疑了一下:“这是……我过去的零件?” 他笑:“是,位于你的肋骨。” 那种动摇如影随形;但两人还是踏上旅程。到处都是静息的死地,自银白过渡到铁灰。他们倒像两粒特殊的尘埃,像余烬在往火里走。 火并不远。骤然间,他们遇见了第一道生机:火山爆发,红亮的熔浆喷涌,像剧烈跳动的心脏。接下来便是火山灰:苍白的、冷却的、熄灭的灰。明明一息之前还像心脏里迸发的热情,也没有更惊天动地的奇观在发生,就这么平淡地步入成灰的结局了。 “和他一起我便看不见灰了,”在灰堆里恋人写下第二封信,“现在我只看到火。我想我们仍在火里。” 前行,一同前行——世界似乎在为他们变好。一片春天中他们走了很远。可在比很远更远的地方,两个人仍只能在春天打转。草木萌发但不生长,浮冰只融化到一半;杜鹃一路都开着,开到要确认那是不是假花。 倦意也沿着花海卷土重来。他们欲言又止,最后还是他先提出:“我们试试分开……分开走一段?” 分开的两个人继续于春天重逢了十七次。一开始在下一个花枝就能遇见;花朵渐渐密起来,要走过一大片才遇见;再后来是走过山、走过林……第十八次见面的时候,他们几乎同时开口:“我很想你。” 春风突然变了,更暖热、更潮湿,带着水星儿;杜鹃也成片成片地凋落了。这时他们仿佛才意识到:那花真美啊。 第三封信就写在花瓣上,一松手,就随初夏的风飘得漫天都是,又在未知的各处轻轻委顿了:像一些渺小的絮语,拼了命地在太过短暂的话音里告知爱。 生命开始变得有限了,他们各自这样想着,应该说再多些,再多些。 但两人终究还是把话在逐渐凝滞的空气里说尽了。世界似乎又从轻微的流动退回了永恒。 恋人突然说:“来吵架吧!” “我们大吵一架!” 当恋人还是机器人的时候,他们从来不曾争吵过。机器人的底层规律是屈从——他突然想,那是爱吗? 如果爱被设定为底层的代码,你屈从的究竟是汹涌的情感,还是冰冷的指令? 吵!争执!恶语相向! 在前所未有的歇斯底里中,一个风暴逐渐成形,席卷而来。狂风肆虐,他们狼狈地向对方嘶吼着,蓦然看见一只鸟歪歪斜斜地从风暴中飞过,像伤口,也像针脚;既流血,也愈合。 在飞鸟落下的羽毛上恋人提笔:“我刚刚才确认那绝非是他为我构建又写入的……它真实地划过我的心了。它属于我自己。” 啊,刚刚。那样长的时间过去了,甚至已经接近永恒,可竟是刚刚确认真实相爱。 前面的景色很快又变成沙漠,一望无际,不辨方向。他取水回来,看见恋人被一群裹着树皮的人围住。 “奇卡奇卡,”那些人发出声音,“奇卡奇卡,奇卡奇卡!” 双方无法沟通,陷入了难解的困境。虽然对方友好地将他们一直送到沙漠边缘,但语言的鸿沟还是无法跨越。恋人试图在沙丘上写字:“奇卡奇卡!”不一会儿,就被吹来的沙子掩盖了。 他问:“你写了什么?” 其实恋人也不知道那是什么:如果一个部落的全部语言只是“奇卡奇卡”,那具体它代表“你是谁”还是“我很饿”,好像都没有区别。或许那也是“我爱你”。 是“附近有绿洲”,恋人答。 在作为机器人的全部时间里,恋人都坦白得一览无余;而人类会伪装。恋人第一次尝试这项技能,并用之于爱人,这才恍然意识到那些甜蜜过往多少沁着些许人类特有的虚伪。自己所爱的那个人类是如此擅长,甚至戏称为“变色龙”都不为过,令曾经身为机器人的自己无法分辨。但现在……他们都是人类了。 接下来的旅途中两个人开始像旧日的角色扮演游戏一样互相较劲。人设换了又换,深情戏码虽然换汤不换药,倒也高潮迭起。谁会先撑不下去?谁才是那个没那么爱的人? 直到他们真的目睹一对变色龙。没有对外界的警戒,也没有对彼此的示威,变色龙只是静静地挨在一起,呈现着近乎一致的本色。 这便是第六封信:一种如无意外还能绵延许久的动物,其本身就是一封耐读的信。他们为这封信拥抱了一会儿。 现在他们已是彼此相爱的、势均力敌的两个人类。可他刚开始爱的时候……爱的是一个机器人。他曾像牧羊人一样左右着这乖巧的机械羔羊。羔羊向他回报以盲从的忠诚,亦步亦趋,不曾稍有偏离。时过境迁,羔羊已不是羔羊。 或许应该让羔羊自己选择一次。 他策划了一次不告而别。 藏在山坡背后,他窥视着恋人的一举一动:阅读了他留下的第七封信,清理了露营痕迹,环视四周,最终向原定的方向走去。没有哭泣,没有愤怒,似乎也没有轻松。 他长出一口气,在荒地上沉沉睡去。 只是命运总这么荒谬。雨后的密林小径昏暗又重复,转过又一个相似的弯,他们又见面了。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着,拨开藤蔓或灌木,踩碎断枝的声音在沉默里显得格外清脆。月亮升起来,他们走到困乏,便点起火堆。垒石灶、收集引火的干柴、煮水,每一件事都透着默契,却不曾有谁先开口。 半寐半醒的时候又下起雨来。他打一个激灵,猛地起身,却看见熄灭的火堆旁被人用焦灰写下:“让我们继续迷路吧。我还想和他多待一会儿。或者让我们再迷路一次、几次,千万次。” 他愣在那儿。傲慢又自卑的牧羊人从未在乎过羔羊的想法,自以为那是驯服。 他怎么能把爱当作是驯服! 他冲入雨中寻找。 淋得湿透的两个人在雨势最盛的时刻相聚了。仿佛被这大雨冲昏了头脑,他们手足无措,也不知该如何表达,干脆就原始地狂奔着,呼喊着彼此的名字,直到筋疲力尽地去泥泞里倒成一团。 原来你早就在这雨里了,原来我也早就在这雨里了!原来我们本不必躲藏的,只要淋湿就好了!只要沉浸,只要赤诚地爱就好了! 泥地里留下了他们重新拥抱的痕迹:两个看不清四肢的模糊人形。 他提议:“应该在这里写第九封信。” “写什么好呢?” “就写:‘我们不要躲雨了’。” 此后的路上雨水更加丰沛,他们没再躲雨过,新生的草木也肉眼可见地繁茂起来。路旁的梨树上落下熟得过头的果实,散发着酒气般的甜香。某个时刻,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停下,仰躺在一片青草地上。 “不走了吧?”恋人问。 “是的,不走了,就在这里变老吧。” “那还写信吗?” “在死去之前——在彼此还能交谈的所有时间里,我们的话语就是信。也许有些时候说不出来什么,也并不说话;那我们各自的存在、我们的家,还有这片草地,都是信。” “除了你我,还会有谁来读吗?” “会有的。只要他们也离开了银色荒原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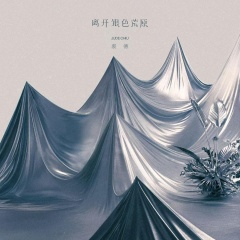


0人评